良渚文化分为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什么特征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菜科解读】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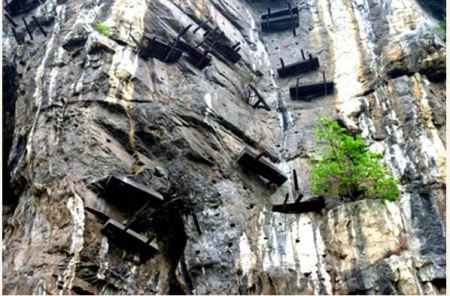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
轮制较普遍。
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
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
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
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
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
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
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
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
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
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
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
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
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
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
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
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
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
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
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
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
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
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
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
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
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

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
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
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
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
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
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
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
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
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
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
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
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
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
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
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
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
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
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
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
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
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
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
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
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
余杭县反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
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

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
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
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
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
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
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
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
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
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
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
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
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
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
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
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
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 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 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
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 雄伟异常, 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m, 控制范围达100多km,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
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势低洼, 沼泽满布, 水草丰盈, 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 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
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
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 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 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
此外, 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 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 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
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节性明显, 夏季山洪暴发, 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 不具备行船条件, 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 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方便运输。
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 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 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 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
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 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 营造生存环境, 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
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即工程材料的制备。
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 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 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 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
“草裹泥”技术, 即先用淤泥堆筑, 外裹黄土。
这些土并非散土, 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 然后码成坝体, 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
随机文章令妃有何「特别之处」?让乾隆第一次临幸时嗨到不行【海狮欧洲史】序:欧洲史上最瞎的第一场暗杀东风5b洲际弹道导弹详解,可携带10枚50万吨当量核弹头蜘蛛神后罗丝前世今生,精灵的命运女神堕落成任性女王带土召唤外道魔像,揭秘宇智波带土会什么忍术
人临死前是会非常平静还是非常恐惧?心理学家的回答很一致
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和感受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在临死前非常平静,有的则充满恐惧。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在临终时的内心状态呢?心理学家们对此给出了一致的回答。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死亡焦虑”。
死亡焦虑是指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不安感,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
有研究表明,对死亡的焦虑程度与个体的人生观、宗教信仰、生活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
比如,在某些宗教中,对死亡有着特定的解释和认知,这可能会减轻个体对死亡的恐惧感;而一些生活经历中的创伤和挫折则可能加剧死亡焦虑。
其次,个体的性格特征也会对临终时的内心状态产生影响。
有些人天生性格内向、沉稳,对于未知的死亡可能更能保持平静;而一些性格急躁、焦虑的人则可能在面对死亡时感到更加恐惧和不安。
除此之外,个体的生活态度和经历也是影响临终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
那些对生活充满感恩、有着积极向上态度的人,在面临死亡时可能更能够接受和平静面对;而那些经历过极端困难和痛苦的人,则可能在临终时承受着更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
另外,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也会对个体在临终时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
在一些文化中,死亡被视为自然的过程,人们对此有着更加淡定的态度;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对死亡有着特定的仪式和观念,这也会影响个体对死亡的感受和认知。
总的来说,个体在临终时的内心状态既受到内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而心理学家们的一致看法是,人们在面对死亡时,往往会表现出多样化的心理状态,有的平静,有的恐惧,这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在临终时的内心感受,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和尊重。
故宫多次闹鬼事件,1992年曾白天惊现神秘宫女?...
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的皇宫,故宫自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无数历史和传说。
有传闻说,在夜晚的故宫中会出现各种怪异的现象,不少人都声称亲眼目睹过故宫的鬼魂。
那么,这些闹鬼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呢?让我们一同揭开故宫多次闹鬼的谜底。
据说最早有关故宫闹鬼的传闻可以追溯到清代皇帝乾隆年间。
当时,有许多人声称在宫殿的深夜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或者看到了皇帝的亡灵穿梭于宫殿之间。
这些传闻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连清朝宫廷内部都充满了惶恐之气。
然而,有些人却质疑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指责这只是一种官方制造的谎言来维护皇权的虚妄。
然而,这些传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来越多的人声称自己在故宫中遇到了鬼魂。
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故宫之所以成为闹鬼的地方可能与其庞大的面积和深厚的历史有关。
故宫曾经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居所,宫殿众多,其中一些甚至存有各种机关和秘密通道。
这样的地方注定会引来各种传说和神秘事件。
另外,许多闹鬼的传闻还与故宫保存着的历史文物有关。
故宫的文物收藏非常丰富,包括了大量的古代器物和艺术品。
有人认为一些古物中寄托着先人的灵魂,因此在夜晚散发出一种诡异的气息。
这些灵魂或许一直在守护着自己曾经的领地,也或许只是因为无法超脱凡尘的束缚而徘徊。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于故宫多次闹鬼并不置信,他们认为这只是人们的臆想或者一种传统的迷信观念。
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已经发达,再没有什么神神叨叨的鬼魂存在。
然而,无论怎样都无法否认的是,故宫所承载的历史和神秘感无疑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幻想和猜测。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关于故宫闹鬼的传闻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
有人声称拍摄到了故宫中奇怪的光影,在照片上出现了模糊的人形。
还有人描述自己在故宫游览时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袭来,仿佛有人在身后注视着自己。
这些所谓的证据或许无法令人完全信服,但也让更多人对于故宫的神秘感和好奇心倍增。
总的来说,故宫多次闹鬼的传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无论是基于信仰还是科学,我们都无法确定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或许,故宫中确实存在着灵异事件,也或许只是人们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
无论怎样,故宫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文化遗产,它所蕴含的历史和传统永远都会让人心生敬畏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