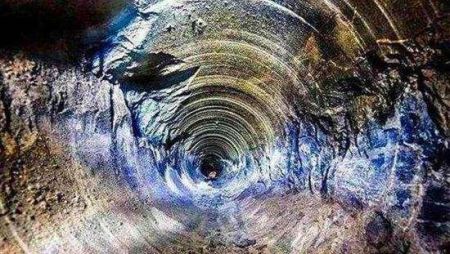水洞沟遗址:科学与人文在这里交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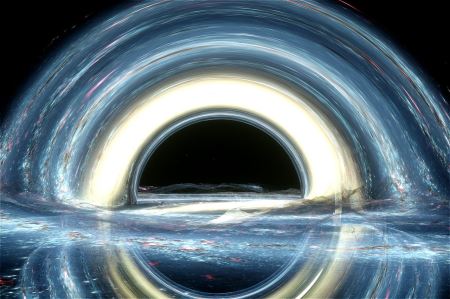
【菜科解读】
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
水洞沟遗址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在中国西北苍茫的毛乌素沙地和滔滔东流的黄河之间,宁夏水洞沟遗址坐落于此。
约4万年前,一群从北方迁徙至此的狩猎采集人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书写水洞沟地区的古史。
其后,陆续有先民到此生产和生活,续写史前文化篇章。
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群仍在这里打石制陶,传递文明的薪火……
1474年,自横城至盐池的长城落成,它成为明代长城的一部分。
1697年,清朝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准格尔部,循长城南侧古道穿水洞沟而过,留下历史的印记。
1923年,两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在水洞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中华大地在远古就有人类生存繁衍,其后学者不断到此发掘和研究。
如今这处古遗址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考古学和地质学的科考基地和人才培养的田野学校、中小学研学的露天课堂。
它也是我国唯一一处以史前遗址为核心的国家5A级景区,是游客体验文化遗产保护的旅游之地。
持续的考古不断深化遗址的文物价值
水洞沟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产地。
该遗址由若干地点组成,散布在黄河的支流边沟河两岸,埋藏着距今4万年至5000年前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不同生存活动所留下的遗物与遗迹,勾画出一幅幅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先民在此迁徙交流、生息劳作、薪火相传的历史画卷。
第1地点最早被发现和发掘。
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根据这里出土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于1925年在国际学术界率先发文,宣布遥远的东方存在旧石器时代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这里出土的石器文化处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向晚期的奥瑞纳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当时发生过东西方人群的远距离迁徙。
其后该地点又被发掘出更多的遗物和遗迹,表明4万年前带有特定技术的人群到此生产生活过,其重要性愈发突出。
这里出土的规范、长薄的石叶制品被认作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西伯利亚广泛分布,在东亚却是凤毛麟角,有学者据此支持现代东亚人群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非洲诞生并自西向东迁徙的早期现代人的后代的论断。
但第2地点给出了不同答案。
这里出现距今3万年前后的多个文化层位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将古人类的生存行为演绎得更加绘声绘色。
该地点的石制品显示出与第1地点不同风格,回归在华北延续了百万年的小石片文化传统,但一些石器加工得规整、精细,说明技术与文化在发展和跃变。
该地点还出土少许精致的磨制骨器和逾百枚用鸵鸟蛋皮制作的经磨圆、穿孔、染色的串珠,表明当时这里生活着一群爱美的水洞沟人。
精致的石器、磨制骨器、装饰品、艺术创作表明这里本土的古人群也已演化进入现代人的行列。
该地点还保留密集分布的火塘,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形成聚落社群。
从石器上提取的使用痕迹和残留物表明,当时的先民已在对特定的动植物资源做深度开发利用。
2017年,在第12地点展开的考古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该地点出土1.1万年前的丰富文化遗存,包括技艺精湛的细石叶制品,精美的磨制骨针,骨梭形器,骨柄石刀,石磨盘与石磨棒,精巧的磨制小圆石饼等。
梭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会织网,以此捕捉飞鸟和快速奔跑的羚羊、野兔,遗址出土的这些动物的碎骨是当时人类的厨余物。
石磨盘与石磨棒在后期的农业遗址中常见,表明农业的雏形在这里出现。
尤为重要的是,经过对遗址大量碎石的多学科分析,发现这里的先民已经在使用石煮法,即将石头烧热,放到水中使水沸腾,把浸在水中的食物煮熟。
对这些遗存的考古发掘和信息解读,显示这里正在实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狩猎采集生计向农业经济的转型,数百万年迁徙游动的栖居模式向定居转变。
这些重要的人类历史过程节点和证据,都埋藏在水洞沟遗址漫漫的黄沙和层叠的褐土下,通过持续的考古不断被发现。
保护、科研、科普、旅游可以互益共赢
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旷野土遗址的可视性和观赏性较差,对社会大众的旅游吸引力不强。
虽然该遗址在考古界早已闻名遐迩,但很长时间这里只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和残垣断壁。
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大众能看得懂、感兴趣,让游客在这里既能得到文化的熏陶,也能获得休闲娱乐的快乐?
#p#分页标题#e#在考古专家建议下,水洞沟遗址博物馆首先建立起来。
水洞沟的管理者到国内外的相关博物馆考察、取经,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并与鲁美艺术学院、沈阳工学院的博物馆设计人员和文物考古专家一起反复研讨、推敲,最终形成了博物馆建筑与展陈设计方案。
在2011年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水洞沟遗址博物馆正式落成对外开放。
遗址博物馆通过图片和雕塑系统地展示了水洞沟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用实物、图片和立体场景复原等手段再现了4万年至5000年间先民在这里狩猎采集、生存繁衍的情境。
博物馆内最具创意和吸引力的展示单元是沉浸式远古生活体验区。
该体验区将声、光、电、幻影成像、动漫、地震平台对接等高科技手段和实景、古环境艺术再现等方式,让游客置身史前环境中,近距离观赏先民制作工具、狩猎采集、载歌载舞的一幕幕片段,身临其境体验狂风骤雨、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难对人类生存的影响。
他们在遗址附近设立古人类生活体验区,为观众表演先民工具制作和资源获取的技艺,让游者亲身体验制作石器、拉弓射猎、钻木取火烤熟肉食,让游客体验远古生存。
教育部门推出中小学研学游项目以来,这里的仿古体验活动成了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在模拟发掘现场学习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流程,了解科学家撰写人类史书背后的故事,领悟到人类演化到现代这一征程的坎坷和卓绝。
在遗址保护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并颁布实施了《水洞沟遗址保护规划》,使遗址的保护、管理、利用和发掘、研究有章可循;妥善处理了在遗址区开展基础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将遗址区内的土长城加以修缮,使水洞沟遗址和明长城这两处国保单位交相辉映。
政府部门与企业在准确理解和掌握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明确了相关方的责权利,明确了旅游资源开发不可触碰遗址本体、不可损毁文物、不可破坏遗址环境、不改变遗址管理权限的原则。
在学术方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遗址做持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发现新的地点和文化层位,不断拓展遗址的文化内涵。
并以此作为田野学校,展开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系统培训,将最新的野外发掘和信息获取技术及理念运用于考古实践,一批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的青年人才不断从这里走出。
学者们围绕该遗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提出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还举办过数次国际、国内行业学术会议,推动和深化了有关史前人类迁徙、技术发展、生存模式等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提升了我国相关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围绕该遗址的考古和学术成果所进行的公共传播,使该遗址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8年,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在这里成功举办,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讲座、石器制作与使用模拟演示、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艺术再现、小小讲解员大赛等形式,普及旧石器时代人类技术、文化和生活知识,诠释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程和伟业,传递珍视和弘扬人类历史的精髓、保护和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理念。
水洞沟遗址的实践模式可概括为: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与企业密切合作互动,各自发挥优势和专长,遗产保护和利用并重,学术与科普互促,最终实现保护、科研、科普、旅游互益共赢。
这种保护实践模式,对其他史前旧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具有借鉴意义。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古时候真实的“摸金校尉”,鬼吹灯是科学现象
别急,在说摸金校尉前,先来说真实的“鬼吹灯”。
“鬼吹灯”现象是科学并不玄妙神秘 据小说《鬼吹灯》的叙述,古人在是盗墓时,需要在墓室东南角点一盏灯。
如果鬼不让你盗墓,就会把灯吹灭--这是一种的活人和死人之间的协议。
不过,现在只要学过中学化学的人都知道“鬼吹灯”的真实原理是这样的: 昏暗的墓室里缺少氧气,盗墓者点一盏灯的目的一是照明,二是只点一盏灯减少对墓室内氧气的消耗,第三就是所谓玄妙的“鬼吹灯了”:墓室内氧气本就不多,如何等突然熄灭,则说明氧气不够,盗墓行为必须暂停。
这就同如今的人们进入长期未开的地窖之前,要先点燃蜡烛,用土办法探测下雨地窖内的含氧量是一个原理。
奈何古人不懂这些化学常识,于是将这种自然现象归结于神鬼之时,就认为是墓中的鬼祟在作怪。
说完了“鬼吹灯”,再说说为什么盗墓者要把这盏性命由关的灯放置在墓室的墓室东南角呢?除了归结为封建迷信的老说辞,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别的科学道理了么? 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剧照 其实,这又与古人的葬俗与人体力学有关了。
中国古代墓葬,除了少部分的高等级大墓外,多半选择坐北朝南的型制,即作为墓室薄弱点的墓门一般朝向南方。
盗墓者处于盗掘方便的考虑,往往也会选择墓门这处薄弱点开展盗掘活动。
盗墓者在掘开墓门之后,往往会随手将照明工具放在一边,开始盗墓。
而正常情况下,由于人体力学原理,人类往往因为“右力”(即右手、右臂等右半侧身体更灵活,力气也更大)的原因,会将重要的物品放在右手中--墓门大开后,在的墓室内,盗墓者最首要的工具自然是照明设备,因此盗墓者用右手持有珍贵的光源(灯、蜡烛、火炬等)的肯能性也是最高。
“墓门朝南”、“右手持灯”、“随手一放”将这些细节重合在一起,便导致盗墓者把灯放置于墓室东南的几率最大。
再结合“鬼吹灯”的化学现象,以及盗墓这种特殊活动的诡异气氛,和古人对自然想象的一知半解,当然还有古代盗墓活动是标准的“口口相传”式的经验学,于是才有了摸金校尉盗墓时在“墓室东南角点一盏灯”的民间说法--后来的盗墓者只是遵从了盗墓前辈们总结出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教条化、神圣化,却并没有思考这些经验学的发端。
好了,言归正题,下面正式来聊聊摸金校尉这个民间传说中非常有钱途的职业。
中国历史上的盗墓非常流行,盗墓者可以是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除了部分故意要惊扰死者的政治复仇,主流盗墓活动的目的都非常明确直接,就是图财。
墓里有宝贝,总会有惦记宝贝的人。
不过,虽然盗墓者众,也不是什么人都配叫摸金校尉。
盗墓源于厚葬,有“宝”即会招掘 盗墓是厚葬的孪生兄弟。
另一个提倡厚葬的古文明埃及,盗墓活动同样很猖獗。
中国人视死如生,活着的时候崇尚享受,死了也不能亏待自己,还要“食太仓”(墓室常见铭文:死了还要享用国家粮仓)。
厚葬之风,几乎与中国历史相始终,即兴厚葬,此后历代,时起时伏,而盗墓之风则与之形影不离。
一方面,墓主人死后要享受,儿孙要尽孝,自然会把大量金银珠宝埋入墓中;另一方面,盗匪、平民、军阀,甚至政府等,又急需钱财救急。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盗墓记载,见于周代末年。
当时有人挖掘古墓,得到了一颗玉印,上面刻有八十个字,最后到了手里,引起了这位学者型官员考辨古文字的雅趣。
早期盗墓者的技术水平,因记载往往语焉不详,不得其详。
盗墓行为是各个阶层都乐意为之的,古代大墓封土又往往巨大而醒目,逮准了猛挖,往往不愁没有收获。
被民间认为是盗墓者的祖师爷 至于专业的盗墓技术,我们可以从清末掌故汇编《清稗类钞》中,略窥一二。
当时中国的专业盗墓客,常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擅长“巧力”,对于盗洞应该打在何处(棺前还是棺尾),打成什么形状(方的还是圆的),都有独特的讲究,并且有一些专业的发掘器械。
因北方汉唐故地,大墓集中,封土巨大,发现大墓并不难,如何快捷的取走东西,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南派盗墓,则更注重“巧技”,尤其是堪舆术的运用。
只有对风水知识有足够的掌握,才能助力他们精准定位大墓的位置,少走弯路。
据说广东帮还有所谓的“望闻问切”四种绝技,其功能大多也还是协助判断大墓的位置。
“盗高一尺,墓高一丈”,造墓与盗墓也在进行着军备竞赛。
最常见的墓葬防范是加固墓室,尤其是早期的诸侯大墓,往往以巨石头砌墙,墙内充填细沙,给盗墓者的盗墓行为增加难度。
长久不得打开墓室,费时费力不说,还容易被发现,盗墓者权衡利弊,自然会选择放弃。
第二种墓葬防范是设置机关,这种方法常见于众多的笔记小说之中,如《太平广记》引《酉阳杂姐》载:一伙盗贼掘开一古墓,进人墓道,“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因列炬而人。
至开东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
还有“见铜人数十枚张目视,俄闻家中击鼓大叫,竟不敢进”等。
除了死人防范盗墓,活人也会帮忙,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死后被打搅。
历代法律对盗墓行为的惩治都极为严厉,动辄死罪。
此外,社会舆论对盗墓行为也是毫不留情,历朝历代的文献中,都不乏盗墓者遭遇恶报的志怪故事。
不过种种防范和法律的惩治,只能对付的了小贼,古代的盗墓主力军,往往并不是他们,而是所谓的“官盗”。
也只有他们,才配叫“摸金校尉”。
“官盗”机器开动的时候,席卷大地,无墓不掘,无骸不露,民间小贼实在是望尘莫及。
你也配叫“摸金校尉”? 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被称为“摸金校尉”,实际上,“摸金校尉”也好,“发丘中郎将”也罢,指代的都是官方“盗墓贼”。
历史上著名的官方盗墓团伙,多为军阀,手下的弟兄跟着你吃饭,军费何来? 最便捷的取财之道自然是盗大墓,的曹操等军阀,伪齐政权的“淘沙官”,五代的温韬,的孙殿英,莫不是如此。
曹操并非是“官盗”的开创者,其实两汉之际,官方半官方的盗墓行为已不少见。
但曹操的很多行为还是比较突出的。
陈琳帮撰写的讨曹檄文难免夸张,但是多少能反映出一些事实真相:首先,盗墓时,曹操往往亲临现场,这与曹操个人爱好有关,他早年即已从事盗墓活动,劣迹斑斑;第二,曹操还设置了专门的盗墓机构,并发明了“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两个专业军职。
某部动漫作品中的著名的“官盗”分子,军阀温韬 不过,所谓的“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名称滑稽,很可能只是一句戏言,或是陈琳杜撰嘲讽曹操的言辞。
“中郎将”在古代是级别很高的军事职位,以“发丘”(掘大墓之封土)命之,可能性并不高。
中级军职“校尉”的命名也是同理,掘坟大队长,捞金小队长,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
至于曹操的盗墓手法,--手法之简单粗暴与民国孙殿英破坏墓如出一辙,发动军队肆意破坏,中原各地的众多大墓都遭到了空前破坏,史载“无骸不露”。
盗墓盗多了,当然也担心盗到自己头上,只好提倡薄葬,并尽量在墓葬外形上也小心低调。
据《·魏书》记载,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即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瘠薄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
后世的很多记载甚至有不少关于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躲过盗墓贼的眼光,当其在2005年被河南人员发现时,已多次被盗。
有曹操的榜样在前,后世的”官盗“自然是前仆后继 唐末五代最著名的“官盗”分子是军阀温韬,此人可称为”摸金校尉“中的无冕之王,人称”贼帅“。
据《唐书·温韬传》记载,温韬曾将”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
另据《》记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
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
钟、王纸墨、笔迹如新。
韬悉取之,遂传民间。
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 两宋时期,随着之难后的宋室南迁,金人扶持的傀儡伪齐政权公然设置了专司盗墓的官职“淘沙官”,这个机构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同于军阀设置的军职机关,而是一个政府盗墓机关。
这个官方盗墓机构发掘了大量的官私墓葬,在帮金人敛财上也可谓是坏事做绝了。
孙殿英盗清陵居然厚颜无耻地盗出了水平盗出了理论 近代的“官盗”例子,不能不提民国军阀孙殿英。
得益于时代的进步,与古代“官盗”同行相比,孙至少有两项重大进步:一是开墓用上了炸药,二是给盗墓套上了理直气壮的理由。
文强的《孙殿英投敌经过》中,记述孙对盗墓行为的解释:他自称祖上是抗清殉国的名臣,“满清杀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像,这样的人,都被开棺戮尸,我虽不才,亦知道佛经有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曾有不少网友疑问,现代的考古发掘,也常开古人的大墓,某种程度上也是吃死人饭,难道就不是“官盗”,不是“摸金校尉”?还真不是。
现代考古为何不是“摸金校尉” 首先,考古学是一门以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综合性科学研究,考古学中涉及的对古墓的发掘,也是以此为目的,与盗墓以售卖随葬品图财根本不同。
第二,考古发掘古墓,不是破坏,而是保护。
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大多成为各级文物,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并有机会陈列在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考古遗址不但能很大程度得到复原,还有望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甚至世界级人类遗产。
“考古和盗墓的区别就是研究矿产地质和偷挖乱采的区别;就是动物学和偷猎虐杀的区别;就是医学和贩卖人体器官的区别。
” 最后,考古发掘也会考虑到在世之人的感情因素。
例如,明清两朝年代晚近,尤其是,距今不久,后人众多,并涉及民族感情。
因此,除非遇到特殊情况,考古人员不会主动发掘明清皇家陵寝。
随机文章英国历史:忏悔者爱德华……他到底忏悔了什么?韩国萨德部署完成了吗,萨德部署完成(中国一半国土在美军监视内)全球最先进agm158巡航导弹,376万美元一枚隐身性能超强长征10号重型运载火箭,最大运载能力达150吨(未实际生产)恐惧魔王迪亚波罗,勾引王子占据身体和灵魂(天堂最大敌人)
意大利考古发现40万年前古人类已利用大象骨头制作各种工具
最新一项考古研究中,来自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考古学家 Paola Villa 和她的同事,对意大利一个有大量大象死亡的地点进行挖掘考古,,并发现了这些人工制作的工具。
研究小组发现,大约在 40 万年前,在这个遗址中,人类利用这些大象的尸体创造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骨质工具--有些工具是用复杂的方法制作的,这些方法在 10 万年后才会变得普遍。
科罗拉多大学自然古代博物馆副馆长 Villa 表示:“在该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骨质工具,但并没有这么多种定义明确的形状”。
该研究将目标锁定在离现代罗马不远的一个名为 Castel di Guido 的遗址。
几十万年以前,这里是被一条短暂的溪流刻出的沟壑所在地,一种有 13 英尺高被称为直牙象(Palaeoloxodon antiquus)的物种会在这里解渴,偶尔也会死亡。
Villa 表示:“在Castel di Guido,人类以标准化的方式折断大象的长骨,并生产标准化的坯件来制作骨质工具。
而这种能力直到很久以后才变得普遍”。
就在 40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刚刚开始在欧洲出现。
维拉怀疑吉多堡的居民是尼安德特人。
Villa 表示:“大约40万年前,你开始看到习惯性地使用火,这是尼安德特人血统的开始。
这对吉多堡来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