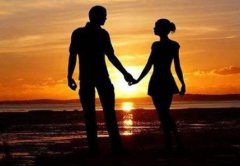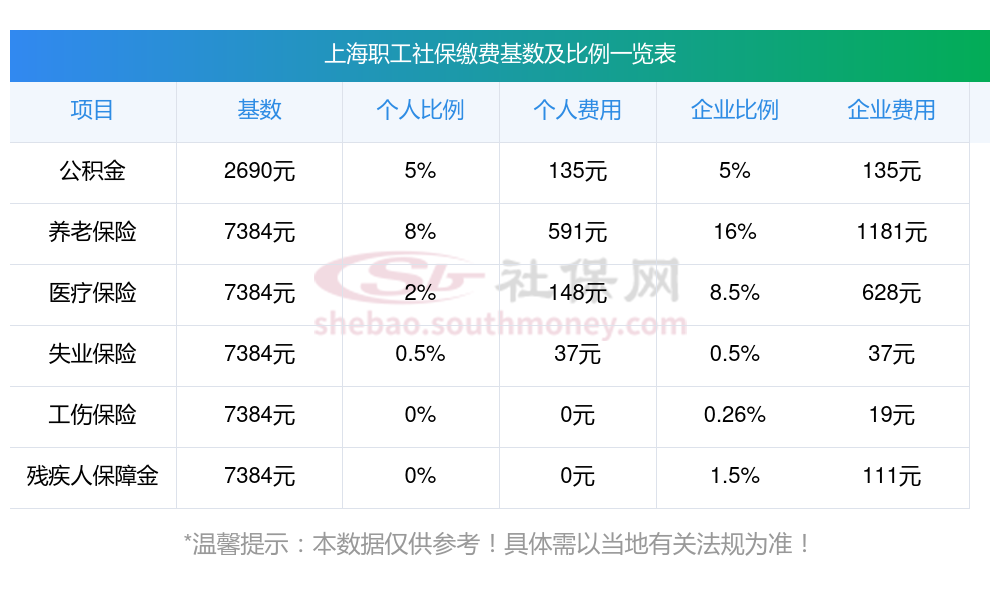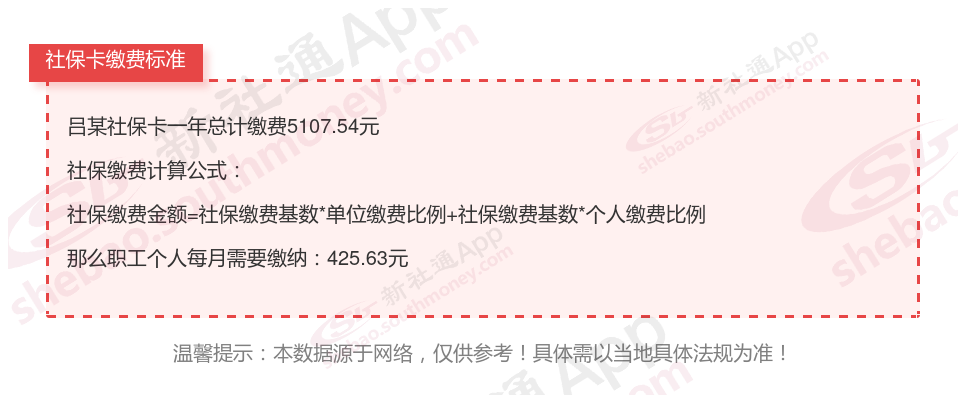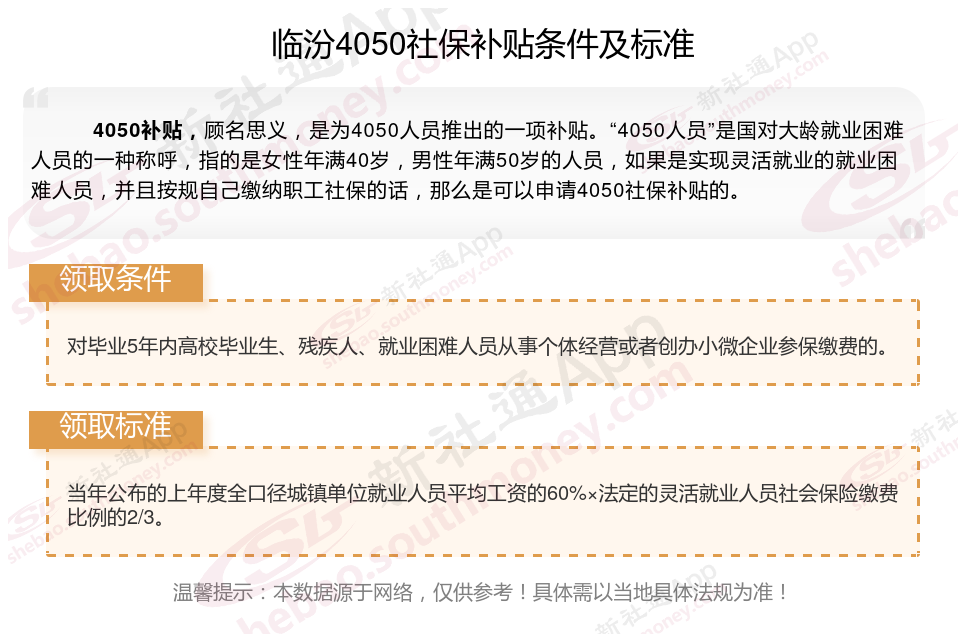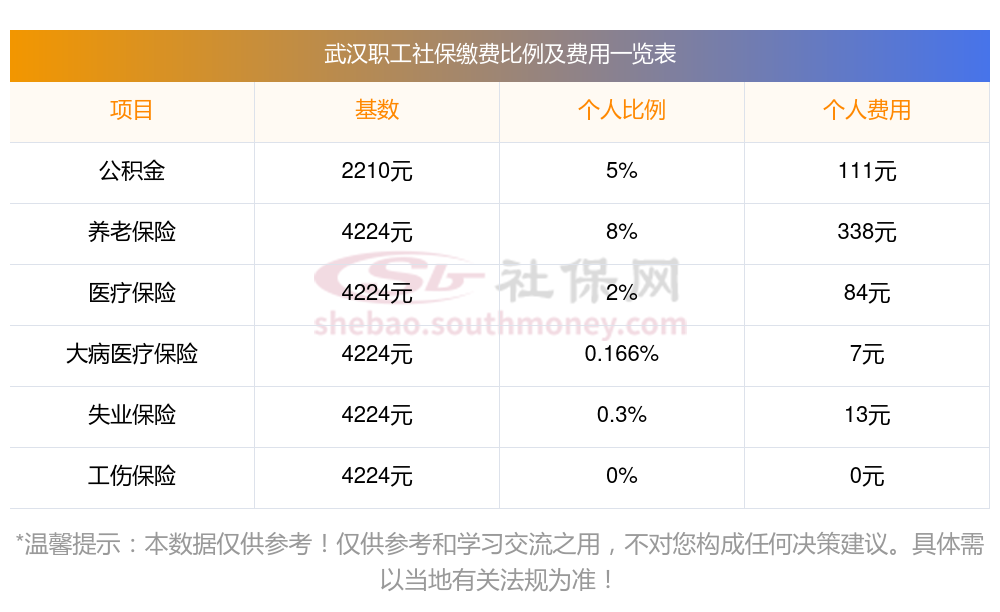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国士无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菜科解读】
网图,侵删

“侠”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一个意象,所赋予其上的精神内涵不断丰富,从最开始的“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逐渐演变成“为国为民”的慷慨悲歌的家国情怀,这是民族精神的不断升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那么被称为“侠”的这一群人,除了武侠小说中塑造的艺术形象之外,历史是否有其原型呢?
一、汉初游侠群体的产生原因
秦汉时期,史料中开始对侠有独立的记载和关注,其中《史记》中甚至出现为游侠单独列传。
此时的“侠”多指豪侠,游侠之类。
他们自身并无官职,但是凭借着其所掌握的社会财富蓄养门客。
这种门客的招揽之风承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以战国四公子为例,他们招揽手段除了经济上的支持之外,更多的是为门客提供更为广阔的政治资源。
这是社会进步,文化下移以及平民政治力量崛起的表现,虽然不乏鸡鸣狗盗之辈混迹其中,但是仍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汉初游侠招揽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这些游侠本就出生于平民,在政府统治秩序的地位中无足轻重。
所以,他们所积聚名望、招揽门课的手段就是钻了制度空子。
西汉初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是百姓生活压力却仍旧不小。
受生产力的限制,汉代百亩之地,所产粮食不足百石。
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认识,可以取一家五口,一年劳作所得的粮食为一百五十石。
汉初的税率为十分之一,也就是上交十五石给国家政府;平均每人一个月的口粮为一石半,一年下来就是九十石。
余下的资产也就是在四十五石,而这四十五石左右的粮食还需要变卖为金钱,每年的祭祀、疾病、等等花费让剩余资产也变得捉襟见肘,赶上上官加税,以及年成不好,又让原本就困苦不堪的农民雪上加霜。
生活窘迫,无奈之下只能卖田给豪强大户,从原本的自耕农转变为租地而种的佃户。
但是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高出国家税率十五倍的地租,农民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最终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董仲舒对此描述的十分贴切“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还是在汉初文景时代所用轻徭薄赋的政策下,所以我们不难想象武帝后期的整个社会的土地兼并的有多么严重。
卖田卖地改变不了生存困境,只能卖儿鬻女、卖了自己。
贫民的生活不断恶化,最只剩下自卖为奴或者亡命天涯两种结局。
汉初蓄奴之风兴盛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
但总有不甘为奴的人热血青年,在颠沛流离之中试图保留自己最后的尊严,便成了亡命之人。
但是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不管境遇怎样都需要融入一个集体中去,才能保持生存。
于是,藏匿这些亡命之人的“任侠”就出现了。
他们不需要亡命之人签订契约或者确定奴仆身份,也不以金钱去购买亡命之人的自由。
单凭义气情谊招揽众人,被招揽的人被称为“宾客”。
当然,这种招揽虽然不求回报,但是“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也必然需要宾客为这些“任侠”两肋插刀。
这些人聚集在所谓“任侠”身边,铸钱盗墓,作奸犯科等攫取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
二、游侠的代表及其社会关系
在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三个“任侠”之中最为有名的三个人,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作“豪侠”。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三人的生平来看看,这些所谓“侠”究竟该如何评价。
首先登场的是身居鲁国故地的游侠朱家,这个人之所以被司马迁记述下来,原因是他藏匿了皇帝亲自通缉的要犯——季布。
季布这个人原本是项羽手下重要将领。
在楚汉战争期间,受项羽派遣多次率兵围困逼迫刘邦。
到了刘邦打败项羽,开创大汉王朝之后,便出巨资悬赏捉拿季布。
此时的季布没有办法,便躲到濮阳一个周姓人家。
这个人将季布打扮成奴仆,以售卖的方式卖给了鲁国游侠朱家。
朱家自然知道季布身份,但是收容季布只是权宜之计,想要从根本上拯救季布的性命,还是需要得到皇帝刘邦的谅解。
于是朱家前往洛阳,拜见汝阴侯夏侯婴。
作为跟随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肱骨之臣,夏侯婴有足够力量帮助季布脱罪,但前提是必须说服他。
夏侯婴和朱家宴饮多日。
朱家乘机对夏侯婴说:“季布犯了什么大罪,陛下追捕他这么急迫?” 夏侯婴说:“季布多次替项羽逼迫陛下,陛下怨恨他,所以一定要抓到他才甘休。
”朱家说:“您看季布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夏侯婴说:“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朱家说:“做臣下的各受自己的主上差遣,季布受项羽差遣,这完全是职分内的事。
项羽的臣下难道可以全都杀死吗?现在陛下刚刚夺得天下,仅仅凭着个人的怨恨去追捕一个人,为什么要向天下人显示自己器量狭小呢!再说凭着季布的贤能,陛下追捕又如此急迫,这样,他不是向北逃到匈奴一去,就是要向南逃到越地去了。
这种忌恨勇士而去资助敌国的举动,就是伍子胥所以要鞭打楚平王尸体的原因了。
您为什么不寻找机会向陛下说明呢?”就这样,夏侯婴接受了朱家的说辞,寻找到合适的时机向刘邦说情,于是刘邦便赦免了季布。
值得一提的是,季布此后也在汉朝政府中做到了一郡太守的高位。
鲁国故地一向是儒家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朱家却以侠士之名而为人称道。
解救季布只是其众多义举的其中之一,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有几百个,其余普通人被救的也多不胜数。
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自我欣赏他对别人的恩德,那些他曾经给予过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
他救济别人的困难,首先从贫贱的开始。
他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得连完整的采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不过是个牛拉的车子。
他一心救援别人的危难,超过为自己办私事。
他曾经暗中使季布将军摆脱了被杀的厄运,待到季布将军地位尊贵之后,他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
从函谷关往东,人们莫不伸长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
在这里,我们抛开朱家自身的品质不说,单说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
首先作为豪侠,他所掌握并购买的奴仆数量不在少数,虽然厉行节约,但是他的经济实力不可小视。
其次,一个平头百姓可以轻易进入侯门之内,并在侯府之内与夏侯婴喝了几天的酒,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在政治地位上拥有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影响力。
同样政治影响力十分巨大的还有同为豪侠的剧孟,他的活动时间是在汉景帝时期。
剧孟是今河南洛阳一带有名的豪侠。
他的行为同朱家的行为大致相同,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活豪士,不求报酬,因此而显扬于诸侯。
他的母亲故世时,前来送葬的车达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等国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七国之乱。
景帝派太尉带兵出征。
周亚夫星夜兼程赶到河南,会兵荥阳。
他到洛阳后,见到剧孟,大喜,说:洛阳得以保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剧孟没有动,也是在我意料之外的,这样看来,荥阳以东不用发愁了。
吴楚举大事不求助剧孟,可见他们成不了大事。
果然三个月内,叛乱平定下来。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会发现,作为豪侠的剧孟此时已经上升到决定叛乱成功与否的关键性作用。
事实上,老书蠡认为此处周亚夫“得一剧孟如得一敌国”的论断不是对于剧孟个人能力的认可,而是其所纠结聚集的势力足以影响一座巨城的归属。
由此可见,起于平民阶层的豪侠群体已经为统治阶级所正视。
读到此处的读者朋友们或许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解,那就是汉初平民豪侠所凝聚的力量是充满正能量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人的例子或许会让我们更加公正客观的审视这一特殊群体。
河内人郭解个子矮小,精明强悍,不喝酒。
年少时残忍狠毒,心中愤慨不快时,亲手杀的人很多。
他不惜牺牲生命去替朋友报仇,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停下来就私铸钱币,盗挖坟墓,他的不法活动数也数不清。
但却能遇到上天保佑,在窘迫危急时常常脱身,或者遇到大赦。
等到郭解年龄大了,就改变行为,检点自己,用恩惠报答怨恨自己的人,多多地施舍别人,少望别人报答自己。
但他自己喜欢行侠的思想越来越强烈。
已经救了别人的生命,却不自夸功劳,但其内心仍然残忍狠毒,为小事突然怨怒行凶的事依然如故。
当时的少年仰慕他的行为,也常常为他报仇,却不让他知道。
但是郭解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豪侠,而不是一个好勇斗狠的街头混混,自然有其过人之处,超高的情商与圆滑的处世手段给了他扬名立万的资本。
郭解姐姐的儿子仗势欺人,为人所杀。
姐姐愤恨,便将自己儿子尸首丢弃在街上,一次羞辱郭解,逼迫郭解抓住凶手。

郭解暗中追查到了凶手踪迹,凶手窘迫,只能面见郭解,解释杀人缘由。
明白了是非曲直,郭解承认凶手行为的正当性“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
”并且放走凶手,把罪责归咎于自己外甥。
洛阳城中有人相互结仇,城中的豪侠出面调解却无法弥合矛盾。
门客们就来拜见郭解,说明情况。
郭解晚上去会见结仇的人家,仇家出于对郭解的尊重,委屈心意地听从了劝告,准备和好。
但是郭解却阻止了他们的行动,而是是等待洛阳城内豪杰再次调解之后再行和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成全其他豪杰的名声,而避免与其他任侠产生矛盾。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
他到旁的郡国去替人办事,事能办成的,一定把它办成,办不成的,也要使有关方面都满意,然后才敢去吃人家酒饭。
得益于这样的处事手腕,郭解的名声迅速传播,甚至获得了政府高官的庇护。
元朔二年(前127年),朝廷要将各郡国的豪富人家迁往茂陵居住,郭解家贫,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因为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
当时大将军卫青替郭解向汉武帝说:“郭解家贫,不符合迁移的标准。
”但是汉武帝说:“一个百姓的权势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这就可见他家不穷。
”郭解于是被迁徙到茂陵。
人们为郭解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
背井离乡肯定会让人难以接受,将郭解名单上报的人是当地的杨姓县掾,于是郭解的侄子杀了这位政府官员以泄愤,只是这样还不够,又将这位杨县掾的父亲也杀了。
杨家人上书告状,有人又把告状的在宫门下给杀了。
汉武帝听到这消息,就向官吏下令捕捉郭解。
不愿坐以待毙的郭解也开始了亡命天涯,得益于多年经营的名声势力,郭解的出逃之路相当顺利。
过了很久,官府才抓住郭解,并彻底深究他的犯法罪行,发现一些人被郭解所杀的事,都发生在皇帝特赦令公布之前,这意味着虽然郭解罪行确凿,但是却无法定罪。
一次,郭解有个儒生陪同前来查办郭解案件的使者闲坐,郭解门客称赞郭解,他说:“郭解专爱做奸邪犯法的事,怎能说他是贤人呢?”郭解门客听到这话,就杀了这个儒生,割下他的舌头。
官吏以此责问郭解,令他交出凶手,而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
杀人的人始终没查出来,不知道是谁。
官吏向皇上报告,说郭解无罪。
但是郭解的行为已经严重挑战了汉朝政府的统治秩序,他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对汉朝皇权的一种挑战。
因此,时任御史大夫公孙弘认为:“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於解杀之。
当大逆无道。
”于是便诛杀郭解全族。
郭解的影响力已经和前面两位豪侠有了明显差别,他有了与政府官吏抗衡的勇气和资本。
无论是他的族人随意杀死县衙官吏,还是宾客杀死因小事而杀死一名儒生。
这种行为无不引起统治者的高度警觉,尤其是此时的皇帝是汉武帝,这位一改前任无为而治的雄主更不会容忍一名任侠挑战自己的权威。
由此可见,郭解之死乃是必然结局。
汉初的所谓“侠”,确实是有豪情义气的一面,但是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序的混乱势力的代表。
其产生的根源是平民阶层中因贫富差距而出现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逃亡的贫民需要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是富民以其财富优势不断扩大影响。
这两种力量各取所需,在西汉初期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催生。
最后演变成郭解这样的社会毒瘤,意图以自己的“私法”取代国家法律。
虽然被司马迁称为“侠”,甚至单独列传,也改变不了其黑恶势力的本质。
总结:“侠”这个字经过几千年的词义演变,从原本的无足轻重,到现在充满着英雄主义的幻想。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应该已经成为现在全部国人的共识,也正是这种上升到拥有着家国情怀的侠义精神,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