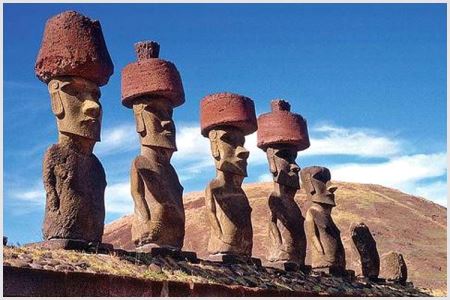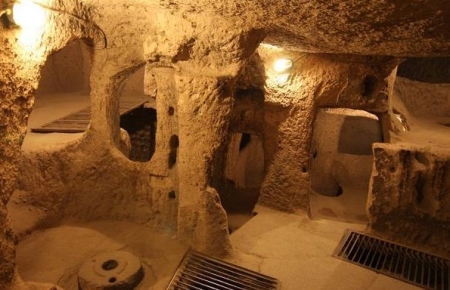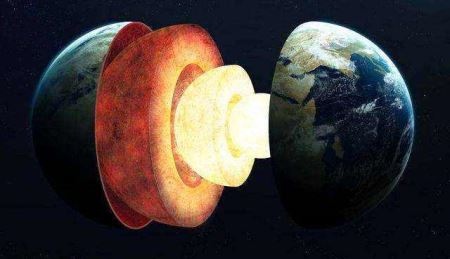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拒绝投降的王朝,面临亡国,坚持死磕到底。

这种独特来自于,当他们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依然选择死磕。
有时候,这种死磕看起来说那么不近常理,甚至感觉有些迂腐。
【菜科解读】
这种独特来自于,当他们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候,依然选择死磕。

有时候,这种死磕看起来说那么不近常理,甚至感觉有些迂腐。
当年率大军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曾派出使臣跟皇帝议和。
李自成提出的条件就是闯军管辖的西北自立,并得到朝廷的封号,还要白银一百万两。
作为回报,李自成愿意掉转枪头,帮助明朝抵御北方的后金。
其实,按照当时明朝的处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封个名号,出一笔银子,免除了两个祸患,将来再图自强,也不是不能接受的事情。
但明朝却拒绝了李自成这个提议,最后崇祯皇帝上吊煤山,明朝就此衰亡,疆域只剩下南边半壁江山。
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
当年在剿灭李自成带领的农民起义军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就曾经提出过,先暂时跟清兵议和,等到将来平定了起义军的内乱后,再慢慢去消灭清军。
也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从当时明朝的情况来看,这个提议确实很务实,可以避免两线同时开战的情况。
而在得知明朝愿意议和后,也表示同意。
但杨嗣昌的这个提议刚说出来没多久,就被否决了。

图为杨嗣昌 从这两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朝这种近乎迂腐的倔强,坚决不投降的死磕。
明朝的这种选择,有一部分来自于明朝在后的选择。
土木堡之变发生在在位时期。
当时明朝因为一次错误的指挥,导致明朝三分之一以上的精锐,损失殆尽。
而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队进犯中原 。
在这个时候,明朝内部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南迁,也就是议和。
一派则是主张。
这两派都各自有自己的道理。
图为土木堡之变 但最终主战派的于谦占了上风。
不仅如此,于谦还在明朝如此危急的关头,重新带领人马,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袭。
明朝也由此避免了南迁的局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于谦以后,明朝如果再谈投降、妥协、迁都,都说统统的不正确,直接处于辩论赛的下风。
而且,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明朝大多数官员,对于后金,都有一种蛮夷的鄙视感在里面。
图为于谦 再加上,明朝的读书人,大多继承了宋代理学的那一套。

而明朝中期“心学”的影响,让这些人在面对国家危急的时候,都想着拼搏一把,而不是临阵退缩。
最为典型的便是黄道周。
当年杨嗣昌主张议和的时候,黄道周反对的十分激烈,并因此被贬官。
但在清军入关后,黄道周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亲自到家乡募集了几千个乡勇,带着仅够一个月的粮食,就上前线阻击清军,时人称为“扁担军”。
以当时清军的浩浩荡荡,黄道周的这个做法,无异于以卵击石。
图为黄道周 就连他的妻子都知道,黄道周这次去,肯定必死无疑。
但他还是选择出发。
后来兵败被俘,在面对清军的劝降,黄道周选择慨然赴死。
临终前,留下“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字。
有时候,确实很难说清楚明朝的这种选择是否正确。
站在利益的角度谋划,这种选择是糟糕的。
但站在文明延续的角度讲,这是一种气节和文化的延续,一种根。
也许,再过几百年后,距离这段历史更远的后人,能够看清它们。
中国传统风俗“初九拜天公"天公是指谁?
“天公”,即。
当这天的子夜(农历正月初八的子时,晚间23时)到来,家家户户会隆重祭拜天公,祈求神明庇佑、延年益寿。
关于祭天与天公的信仰已相当久远,可追溯至远古的夏商时期。
远古时期的人们,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以及敬畏大自然的力量,因而敬天畏天,衍生出天神崇拜,将“天"视为创造万物的神。
殷商时期,商人除了有祭祀人鬼(祖先)、敬天神地祇外,更有完整系统的祭天仪式。
而“天"也是卜辞卜问的对象,来年的收成、吉凶祸福,乃至于国家大事都要询问“天"的意见。
“天"原本没有具体形象,但因被赋予象征宇宙万物的至高存在,被进一步神格化、帝王化,便将人世间的帝王形象套在“天"身上,开始用“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玉皇上帝”等各种称呼“天"。
而人世间的帝王,也借用“天"的概念,称己“受命于天”、“天命在身”,自称为“天子”。
《尚书.召诰》有载:“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召诰》是周召公委托上书,告诫应当敬德,使周的天命能够长久。
可看出周代具有浓厚的天命观,而“天命”也成为中国各个朝代君主最为看重的事物,最后形成天命思想。
形成于时期的,将“天"迎至道教神仙界中,民众皆以“玉帝”为神中至尊。
而玉帝所呈现的形像,多是穿着秦汉帝王的冕服,但这头戴十二旒冕冠、身穿大裘的玉帝样貌,是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定型的。
但是天公地位太过崇高,让一般民众不敢随意擅自为其雕塑神像,多以专供天公的香炉─天公炉代替,因此各个庙宇皆设有天公炉,在祭拜庙宇主神之前,都要先朝外拜天公。
天公的信仰,不仅在毛泽东在《沁园春•雪》提到:“欲与天公试比高”,在日常俗语中处处可见,像是“姻缘天注定”,“天意难为”,流传甚广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歌词也称:“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随机文章奈良时代简介大魔王贝利尔,曾是撒旦人选能力最强的堕天使之一ufo为什么都是圆的?阻力更小/转向升降更灵活(科学分析)南极为什么比北极冷,海拔更高/热量交换少/平均气温低20℃以上地震为什么预测不到,动物异象预测真的靠谱吗/准确率极低
中国科幻作品的艰辛历程,“姓科还是姓文”
2019年《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然而中国科幻的元年应该是1978年。
1978年,大量科幻作品被译介进中国,《未来世界》、《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科幻影视的引入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科幻旋风。
也是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宣告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
这之后,中国大量科技、科普类出版社、科普报刊恢复正常工作,很多作者投入科幻小说创作中。
后来以纪实文学闻名的叶永烈正是中国科幻界的四位大师之一,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复兴;郑文光在大陆被称为“中国科幻小说之父”,他50年代就致力于科幻创作,70年代重新投入创作,发表了多部重要科幻作品,1980年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成员,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曾被改编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电影;萧建亨淡出科幻界后由诗坐稳了第四把交椅。
鼎盛时期有一百余位科幻作者,发表了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说,长篇科幻小说也有几十部。
” 但是科幻作品应该背负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在当时成了一个议论的中心。
时至今日,科幻作品的定义也没得到普遍认同,在当时的中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姓科还是”的讨论。
1979年,《中国青年报》刊登《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批评叶永烈的小说是“伪科学”,会毒害青少年。
并认为限定给少儿看的科幻小说不适合写爱情、犯罪、社会反思的,否则就是低级趣味。
于是双方开始论战。
科普派坚持科幻文学应该承担传播科学知识的任务,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态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这场论战应该止步于学术界,但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有重要地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加入战局后,情势发生变化。
他赞同科普派,主张科幻小说必须承担科普义务。
1980年,钱学森曾批评:“现在有些科普文章和某些流行的科学幻想小说,我看在思想上和科学内容上都有些问题。
”1981年,针对科幻影片,钱又批评:“科学幻想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幻想。
……应该搞那些虽然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但能看得出苗头,肯定能够实现的东西。
……现在搞科学幻想片,太长远的东西是次要的,主要应配合四化,搞2000年的嘛。
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到了2000年是个什么情况,要给农民一个远大的理想,这是个好题目。
”该批评被《人民日报》刊发后,影响很大。
叶永烈的高产被认定为赚稿费、唯利是图。
魏雅华的成名作《温柔之乡的梦》写机器人妻子对主人百依百顺,温柔之极,却不能让人满意。
被批评为“反”、“一篇下流的政治小说”。
而这还不足以团灭中国科幻,真正的严寒即将来临。
1983年,中国科普界某些人本来就看不惯科幻小说,借助于当时的形势把科幻小说列为清除对象。
本来姓“科”还是姓“文”的讨论升级为姓“社”还是姓“资”,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
当时以钱学森为首的科普派批评科幻作品,1983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1980年,我曾向所谓科幻小说放过炮,认为有些根本不是科学幻想,而是荒诞、离奇,没有科学根据的无稽之谈,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
” 也是在这年,遭到重点打击的叶永烈决心离开科幻界,科幻文学大师郑文光因脑溢血结束创作生涯。
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噤若寒蝉。
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
中国科幻进入了10年的冰冻期。
直到1996年以后,钱学森才不再公开批评科幻文学,但此时中国科幻已经断档,连土壤都已经不复存在,日后成为中国科幻领军人物的刘慈欣手握作品却找不到可以发表的地方。
中国科幻界再次迎来春天是在上世纪末,1999年,《科幻世界》杂志发行,刘慈欣这一批新生代作家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幻的春天。
随机文章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威力惊人,导弹可摧毁120座中型城市广州不明飞行物悬浮湖面,引8万人讨论10%的人相信是真地球灭亡后我们人类能够去火星么,马斯克火星移民好处多多为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连爱因斯坦都发现障碍物后面的神学家探索时间漏洞可以穿越,扭曲光线停歇时空穿越时空(打破时间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