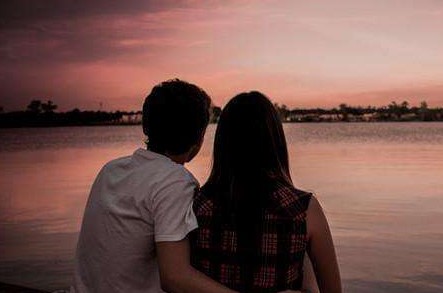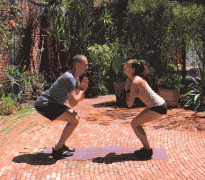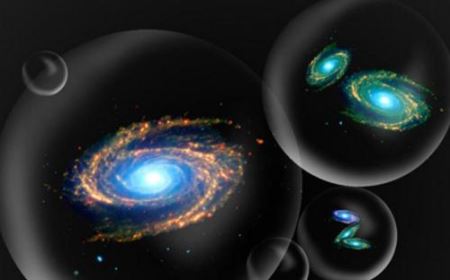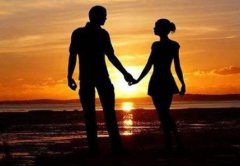34岁素食主义者患上高血脂,原来高血脂饮食忌讳这么多

他感到非常不解:难道不是越胖的人才会得高血脂吗?自己才34岁,还很年轻,而且个子瘦,平时也坚持素食主义,怎么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高血脂?其实小王和很多人一样,对高血脂存在很多的误解。
误解一:认为年纪大了
【菜科解读】
小王看见化验单上向上的箭头时,心里一惊,仔细核对过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参考范围之后,不太能接受的自己患了高血脂的事实。
他感到非常不解:难道不是越胖的人才会得高血脂吗?自己才34岁,还很年轻,而且个子瘦,平时也坚持素食主义,怎么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高血脂?其实小王和很多人一样,对高血脂存在很多的误解。
误解一:认为年纪大了才会得高血脂。
小王的想法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但其实,它与年龄没有直接关系,与运动量偏低,饮食摄入能量过剩有关。
年纪越大患高血脂的风险越高并不意味着年纪轻就不会得了。
高血脂的患病趋势也是逐渐年轻化的,现在小孩子也有很多高血脂的患者。
往往年轻人的高血脂都是因为生活、饮食习惯不良导致。
要注重低糖、低脂的饮食,多吃蔬菜、粗粮;坚持体育锻炼,多运动,避免熬夜。
高血脂的饮食禁忌繁多,小王虽然吃素食,他饮食中虽然限油和肉,但主食和酒并没有限制。
如果不戒酒,不减少主食摄入,其实还是会存在高血脂的风险。
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也是引发高血脂的元凶之一,大量摄入的精致碳水同样会热量超标,多余的热量也会转变成脂肪存储在起来,会直接导致肥胖和高血脂。
误解三:认为得了高血脂只能吃素。
只吃素,豆类、肉、蛋和奶不吃是不行的。
肉、蛋和奶是人体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的主要来源。
长时间这样的营养不足会直接导致免疫功能下降甚至引发疾病。
缺少肉食,胆碱和蛋氨酸缺乏会导致肝脏运输脂肪的能力受损,这也是为何吃素的人也会得脂肪肝。
血脂主要包括两大类,甘油三酯和胆固醇。
说起胆固醇高,很多人立刻就把蛋黄打入冷宫。
然而蛋黄并不是引起高胆固醇血症的主要因素,高胆固醇血症需要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但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周1~2个鸡蛋对胆固醇的影响并不大。
高血脂患者可适当食用少量鸡蛋,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就够了,也不会引起血脂过高的异常加重,而且还能保证营养的供应;应保证营养充足的基础上,适当的减肥、节食,并在必要时使用降血脂药物。
误解五:认为瘦就不会得高血脂小王这种身材瘦削的患病确实也相对少见,但我们不应以胖瘦论血脂高低,因为它和遗传也有一定关系,如果有家族史,那么瘦不瘦已经不太重要了,后代患病几率注定会比别人大一些。
我们有所耳闻但又不是真正了解的疾病,不要想当然地去理解,更不要不误解后告诉他人,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您还有哪些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关注南方健康,三甲医院医生顾问持续为您提供专业的健康知识!
十大知名家养素食宠物:仓鼠上榜,毛丝鼠居榜首
2.缅甸陆龟 缅甸陆龟是一种草食性印度陆龟属乌龟,主要栖息在山地、丘陵和灌木丛中,主要喜欢在夜间活动,背甲长度在20-40厘米之间,体色呈淡黄褐色,四肢上分布有不规则的黑色斑点,背甲上大大小小斑驳的黑斑也是这种乌龟最具特色的地方。
3.仓鼠 仓鼠是啮齿目仓鼠亚科动物,体长在50至340毫米之间,是温带陆生动物,喜欢将食物暂时封存在口中,在人工饲养时以植物的嫩茎、叶、果实进行喂食即可,因饲养仓鼠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空间,因此也深受城市人们的喜爱。
关键字:宠物
十大养生素食加盟店排名 素食店加盟哪个靠谱
而养身最好的习惯无疑是多吃素,市场上也相应涌现了很多知名的养生素食加盟店。
接下来,小编将为大家带来十大养生素食加盟店排名,一起来看看。
10.一叶一世界素食火锅佐丹力159素食全餐属于现代养生餐厅,目前在国内的门店总是有60余家,菜叶说说,食材种类多达150种以上,均是绿色无污染的天然食品,也很好的体现出了品牌的素食养生主义,加盟费在10-20万之间。
8.成素素食临湖素食起源于日本,是一家专门经营蔬菜、豆制品等素食的餐厅,味道非常的纯正,致力于最好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非常推荐给大家,加盟费在10-20万之间。
6.觉西园素食餐厅觉西园素食餐厅在全国的连锁店非常多,品牌致力于素食文化的发展,为地球环境做出了许多功效,同时也能烹饪出养生又可口的美食,加盟费在5-10万之间。
5.花开素食花开素食起源于北京,是一个专注于素食菜式的餐厅,目前在国内的门店总是达到了200余家,其菜式中品种非常丰富,不仅有可口的传统中式美食,还有各种甜点和饮品,加盟费在10-20万之间。
4.膳缘居膳缘居起源于武汉,是一个结合了东西方特色的素食餐厅,这里的各种小微盘和食材都是以天然蔬菜植物为主,特别推荐他们家的素排骨、素鱼块、素牛肉,加盟费在10-20万之间。
3.茶素味素食茶素味素食在国内餐饮领域是非常出名的,它有独特的工艺和品质,成为了素食界的代表餐饮品牌之一,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经营标准,加盟费在10-20万之间。
2.素百味素芳斋专注于当今市场上的潮流饮食,以健康的素食为特色,讲究天然、健康、绿色,烹饪方式也非常多变,还有纯素仿荤菜的做法,非常具有特色,加盟费在30-50万之间。